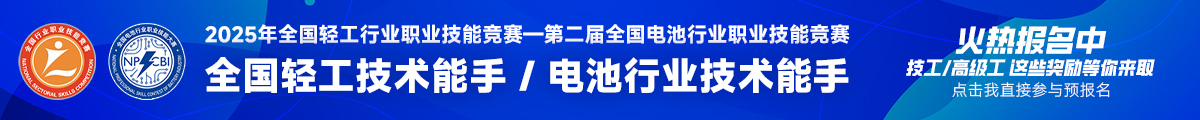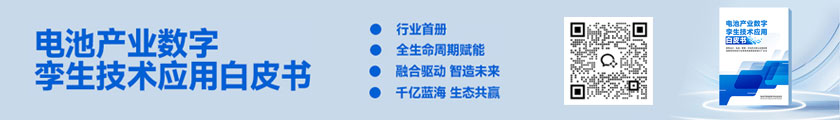ST长园高层“闪电”更迭:控制权迷局与45亿市值的救赎难题
一、高层 “闪电” 更迭:五个月内的管理层大震荡
2025 年 9 月的长园集团,以一场戏剧性的高层变动揭开危机序幕。9 月 27 日,公司公告显示,新任董事乔文健于 9 月 25 日刚当选董事,仅隔 1 天便提交总裁辞职报告,其任期从 4 月 29 日接任至 9 月 27 日不足 5 个月,成为公司史上 “最短命” 总裁之一。而就在 15 天前的 9 月 12 日,董事长吴启权已因 “个人原因” 辞去包括子公司在内的所有职务,彻底退出公司治理架构。
这场动荡并非偶然。回溯至 5 月 1 日,职工代表董事王伟、姚泽同步辞职,姚泽还卸下财务负责人职务,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在半年内近乎 “大换血”。管理层频繁变动的背后,是公司内控缺陷暴露后的连锁反应 ——2025 年 4 月,长园集团因 “董事长控制企业占用资金” 被实施 ST 处理,成为 A 股市场内控失效的典型案例。据公告披露,吴启权控制的运泰利控股通过第三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,2024 年末余额仍达 2.64 亿元,虽已退回 2.45 亿元,但剩余 2159 万元需至 9 月 30 日前清偿,其辞职时点与资金清收节点高度重合。
二、控制权三十年博弈:从李嘉诚到格力金投的 “失控” 轮回
长园集团的治理危机,根植于其长达三十年的控制权更迭史。1986 年由中科院创立的这家企业,1996 年因债务危机引入李嘉诚旗下长和投资,后者以债转股持股 51% 并主导大规模并购,推动公司 2002 年登陆上交所,2014 年营收突破 33 亿元,较入股初期增长超百倍。但长和投资在 2007-2014 年间持续减持清仓,累计套现 27 亿元,斩获 45 倍回报,也为股权分散埋下隐患。
2014 年长和退出后,控制权争夺战正式打响。沃尔核材创始人周和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27.45% 发起要约收购,公司管理层则联合吴启权等成立藏金壹号基金,以 24.21% 持股形成对峙,这场拉锯战持续四年才以双方和解告终。2018 年格力集团曾计划收购 20% 股份未果,其子公司格力金投转而持续增持,目前以 12.98% 持股成为第一大股东,但始终未能实现绝对控股。
股权分散导致的 “无实控人” 状态,成为公司治理的致命伤。格力金投虽意图通过掌控董事会彻查资金占用等问题,但在分散股权结构下难以推进,截至 9 月末,公司前三大股东持股合计不足 30%,中小股东与大股东的利益博弈进一步加剧内控混乱,这也是吴启权能长期通过关联方占用资金的制度性根源。
三、ST 摘帽困局:45 亿市值背后的三重生存挑战
截至 9 月 29 日,长园集团股价报 3.44 元 / 股,总市值仅 45.37 亿元,较 2015 年高点 28.47 元 / 股缩水超 87%,昔日 “新能源明星” 沦为 ST 股。当前公司面临的挑战直指生存核心:
财务修复压力空前。业绩数据显示,2019-2024 年公司净利润经历 “巨亏 - 微盈 - 巨亏” 的剧烈波动,2024 年营收 78.74 亿元同比下滑 7.22%,归母净利润亏损 9.78 亿元,连续两年扣非净利润为负。更严峻的是法律风险 —— 子公司长园和鹰 2016-2017 年虚增利润 3.02 亿元,2024 年一审被判赔偿 3.45 亿元,相当于 2023 年净利润的 3.97 倍,公司虽计划上诉但资金压力陡增。
内控整改任重道远。根据 2025 年 ST 摘帽规则,规范类 ST 公司需解决资金占用并经会计师专项审核。尽管公司已收回大部分占用资金,但年审机构指出的 “资金审批、合同管理、关联交易” 三大缺陷仍待修复。对比 ST 天目因解决资金占用 1 个月完成摘帽的案例,长园集团还需证明内控体系的持续性有效性,审核周期可能延长至 3 个月以上。
新能源业务优势流失。曾几何时,长园集团在锂电领域布局亮眼:中材锂膜 10 亿平方米基膜产能居全球前三,长园深瑞储能装机量国内前三,参股金锂科技供应头部电池厂。但 2024 年锂电行业产能过剩背景下,公司新能源业务营收同比下滑 12%,毛利率从 28% 降至 19%,核心资产的盈利能力持续弱化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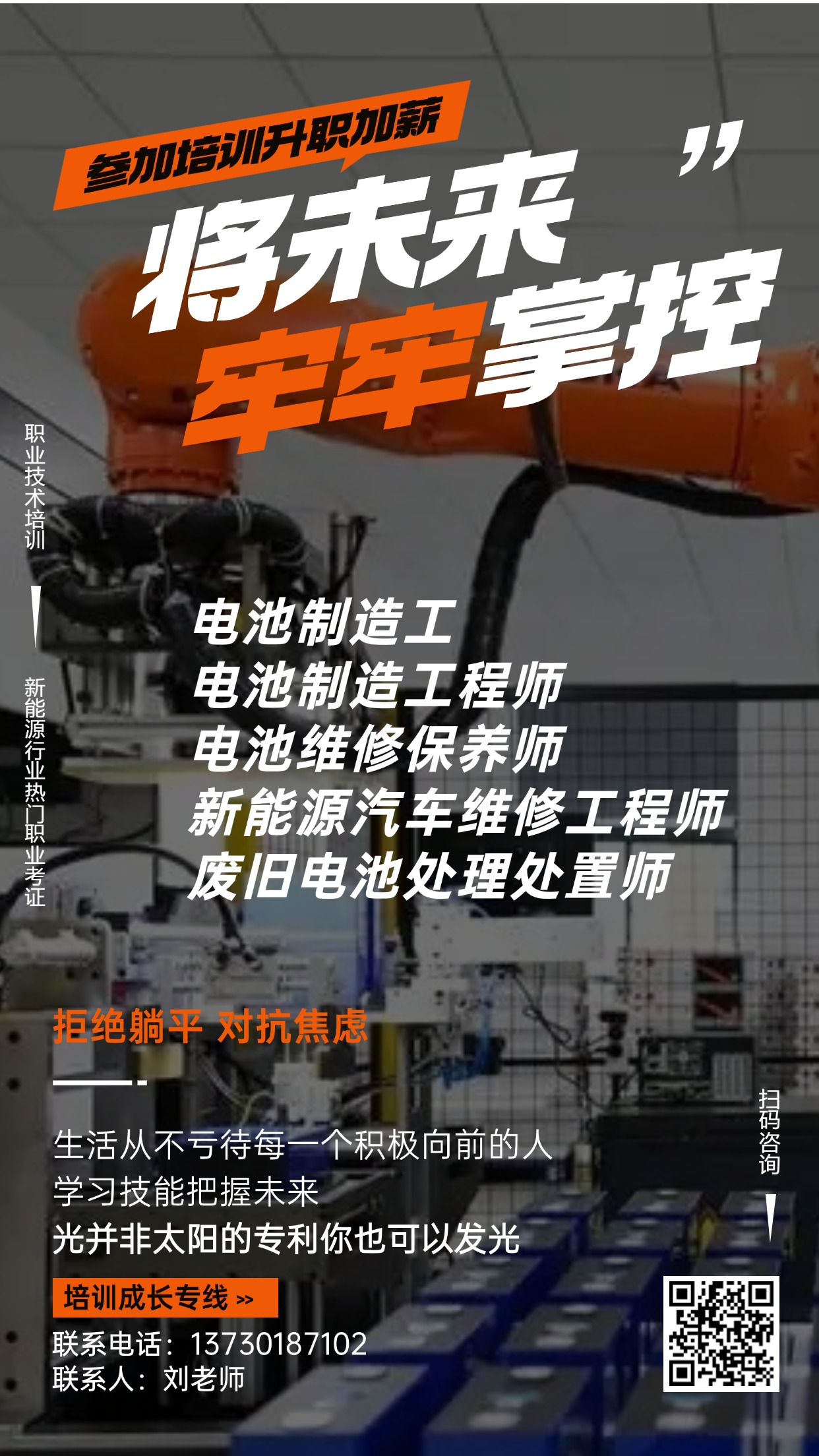
凡本网注明 “来源:XXX(非中国电池联盟)”的作品,均转载自其它媒体,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。
如因作品内容、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,请在一周内进行,以便我们及时处理。
QQ:503204601
邮箱:cbcu@cbcu.com.cn
-
电池的“阴极”是正极还是负极?为什么总有人傻傻分不清?
2025-09-26 10:32 -
原电池、电解池、腐蚀电池:从生活例子看懂核心原理
2025-09-24 11:18 -
我们只知道电池的“循环寿命”,那你知道电池的“日历寿命”吗?
2025-09-24 10:25 -
锂电池的DOD(放电深度)如何影响寿命?
2025-09-19 09:12 -
电池制造工程师培训之电池的材料硅基材料
2025-09-12 09:31 -
透视关键矿产地缘博弈!白旻博士峰会上解析:动力电池回收是中国资源安全的战略破局点
2025-09-12 07:56 -
最高可获5000元补贴,广州市3亿元汽车消费补贴即将启动
2025-09-15 08:56 -
德赛电池主动安全技术突围:以 AI 电芯重构储能安全范式
2025-09-12 09:23



 微信公众号
微信公众号